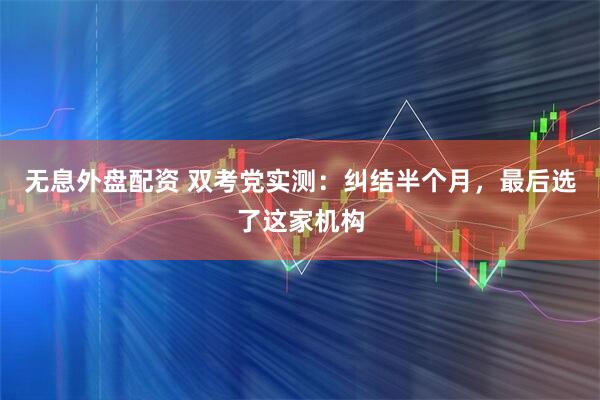创作说明:本文是基于历史的基本情况正规实盘配资公司,开展的二次文学创作,部分属于虚构内容,仅供娱乐,注意甄别,图片为ai生成。
夏朝第15王 姒廑, 夏朝正统君主, 扃之子,
01 西河的最后一次霜降
当廑王醒来时,窗棂上结着今年最后一片霜花,他盯着那层薄冰看了好久,直到侍从轻轻催促,才发现天色已经大亮, 窗外是西河的王宫,瓦当上挂着化雪的滴水,远处能听到筑墙奴隶们抬石头的号子声,他今年刚满五十岁,可身体就像这片霜花一样,轻轻一碰好像就会碎掉。
「王上,东夷的贡品又少了三成。」司贡的官员跪在榻前,声音里满是害怕。
廑王没有回应。
他想起8年前自己刚迁都到这里的时候, 那些部落首领还挺恭敬地献上兽皮和铜料,现在连敷衍都懒得去做了,他摆摆手让官员退下,手缩回被褥时,碰到一块冰凉的玉圭,那是父亲扃留下来的遗物,上面刻着姒姓家族的徽记。
展开剩余91%「父亲」,他对着空荡荡的殿宇小声说道「您说这守成之治,到底守住了个什么?」
02 老丘城的晨雾
廑出生在老丘城的王宫里,具体是哪一年已经没人能准确知道了,那时候是夏朝统治力还能够保持的时候,他的祖父泄王正在忙着整顿部落关系,给畎夷、白夷的酋长加封爵命, 他的父亲扃那时候还是太子,每天在朝堂上学习怎么保持这个庞大联盟的运转。
姒姓王族的宫殿和诸侯的茅屋没多大不一样。
廑的母亲是个身份不清楚的妃嫔,生下他没多久就因为生病去世了, 他被老宫女养大,穿着粗麻布衣服,吃着粟米饭,在宫殿的石阶上摇摇晃晃地跑,老丘城的晨雾常常长时间不散,笼罩着这座用夯土建成的都城。
他四岁那会儿,叔祖父不降王把王位让给了他父亲扃,宗庙里面举行让王的仪式,廑被乳母抱着,躲在廊柱后边看,不降王把代表王权的玉圭递给扃手里,声音苍老还疲惫地说,「这天下越来越难管了,你弟弟也许能比我多撑几年。」扃跪着接过玉圭,额头碰着说, 「 臣弟一定会尽力。」
那时候,廑看见他父亲眼里没有高兴,只有深得看不到底的担忧。
扃王还真是个稳重的君主。
他接着兄长的政策,不瞎折腾,不随便往前,每天处理朝政到深夜,廑被送到王族学堂,和堂兄弟们一块儿念书,他的堂兄孔甲比他大三岁,脾气火爆, 常在练射箭的时候和人吵架,而廑就安静很多,他更爱坐在角落,听老史官讲夏朝的历史。
「太康失国,少康复国」老史官用干巴巴的嗓音说道, 「我们姒家的王权,一直是用血和盟约换来的。」
廑问,「那要是诸侯不想再给血和盟约了怎么办?」
老史官愣了一下,摸着他的头说,「小子想得多,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。」
可廑已经看到了。
老丘城外的农田中,奴隶们脊背上的汗水,市集里,来自有鬲氏的商人抱怨贡赋过重, 朝堂上,东夷的使者眼神越发傲慢,他十五岁那年,父亲扃王在朝会上摔碎了一个陶簋只因为淮夷的贡品里,铜块少了一半。
「他们觉得夏后氏的刀不锋利。」扃王的声音在殿内回荡。
廑站在角落里,看见父亲花白的鬓角和颤抖的手,那时他知道,这个叫做夏朝的庞然大物, 正在从内部慢慢腐烂。
03 青铜铭文里的学徒时光
廑二十岁的时候,他父亲任命他为司农小吏,负责督察都城周边的耕作。这是个不太起眼的职位,然而他做得很认真。天不亮他就出城,光着脚走在田埂上,观察奴隶们怎么引水灌溉,怎么翻土播种。他发现了一个问题:老丘周边的田地经过多年耕种,已经变得贫瘠了。
那天朝会结束后,他第一次主动去见父亲,说道「老丘的地力都衰竭了,粮食产量年年下降,再不迁新都,连王室的口粮都难以保证了。」
扃王从竹简里抬起头,盯着他看了好半天,说道「迁都,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?要重新筑城,要重新分配土地,还要让那些部落承认新的王都。」
「可要是不迁的话。」廑的声音很轻,但每个字都十分清晰「连眼前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。」
扃没有采纳儿子的建议,但从这以后,开始让廑参与更多政务。廑跟着父亲接见诸侯,记录盟约,学习如何在各方势力之间周旋。他发现,父亲就像一个走钢丝的人,对东夷太强硬,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反叛;太软弱,他们又会变本加厉。
廑二十五岁那年,娶了有莘氏的女子为妻。婚礼依照夏礼举行,新人各自拿着半块玉圭,在宗庙中将两块玉圭合二为一。廑握着妻子的手,感觉那块冰凉的玉仿佛在提醒他:从今往后,他的性命不再只属于自己了。
他的妻子问他「你害怕吗?」
廑有点不明白「害怕什么?」
「害怕当这个王?」他的妻子说, 「我听说,不降王就是因为害怕孔甲担不起,才把王位传给他爹。」
廑沉默了挺长时间「我害怕的不是当王, 而是当了王之后,发现什么都没法改变,」
那一年,叔父不降王去世了, 临死的时候,他把廑叫到床前,那苍老的手抓着侄子的手腕说,「小廑啊,你父亲把国家守护得挺好,可光守护并不能长久,夏朝得变革,但又经不起大乱。」
廑跪在床前问「叔父,那我该怎么办?」
「小心孔甲」不降王的声音更轻了, 「那小子心气太高,肯定会栽跟头的,还有……记得,诸侯的心,得用血和德一块儿拴住……」
不降王去世后,孔甲在葬礼上公开抱怨父亲没把王位传给他自己, 他拍着腰里的青铜剑说,「凭什么是叔叔坐这个位子,难道我还不如他吗?」
廑站在旁边,看见诸侯们互相交换眼神,那些眼神里有同情,也有算计。
他头一回知道,王位不只是权力,还是一个靶子。
04 西河岸边的选择
姒廑到三十岁那一年,他父亲扃王去世了,临终之际,扃把玉圭传給他, 只說了這麼一句話,「迁都西河吧,那裡土地肥沃,而且离东夷也更近一些。」
廑捧著玉圭,在父亲榻前跪了很久,他想起自己十五岁那年提出的迁都, 原來父亲一直记着,
继位仪式很簡單
夏朝已拿不出太多资源來制办盛大的典礼了,廑穿上麻制的王服,戴上玉冠,接受群臣的朝拜,孔甲站在第一排, 腰間的青铜剑換成了更新的款式,眼神里的不服好像火一样燃烧着。
廑元年己未,他宣布迁都
當命令下時,朝堂就像炸開了锅, 老臣們全都跪了一地,「王上,老丘可是祖宗的根基所在,怎麼能輕易丢弃?」「迁都耗費巨大,如今国库空虛,恐支撐不起。」
廑坐在王位上面,头一回行使着王的权力, 他平平地说,「老丘周边的土地已经养不活都城的人,西河那边土地很肥沃,而且靠近铜矿,既可以解决粮食问题,又可以铸造兵器,你们是想要就这样困死在这里,还是想要为夏朝续续命?」
再没有人敢提出反对。
廑明白,他们反对的不是迁都,而是他这个新王,他太年轻,还不爱说话, 既没有什么大的战功,也没有强硬的办法。
迁都的事折腾了一整年。
王室、贵族、工匠、奴隶,好几万人大张旗鼓地往北迁移,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,没有乘坐马车,而是和士兵们一块儿步行,他的妻子抱着三岁的儿子,跟在他后边, 那孩子身体虚弱,常常生病,廑担心他到不了西河。
安阳汤阴的西河,挨着洹水,那里土地确实挺肥沃的,却一片荒凉,廑亲自带着工匠规划都城, 划分出宫殿区、作坊区、墓葬区,他天天在工地上跑,脚底都磨出了血泡,还和工匠们一起睡在窝棚里。
孔甲来看过他一回,站在远处冷笑着说,「王兄这是亲自当起工匠了?」
廑擦了擦额头的汗说,「堂兄要是有时间,不妨来帮忙筑城。」
「我并不是干体力活的人。」孔甲转身就走,「王族得有王族的样子。」
廑看着他的背影也没说什么。
西河城建好之后,廑把王宫设在最中心, 这是他所设计的王宫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壁垒,而是被作坊和市集围着,他说「王要是想要听到百姓的声音,就不能离他们太远,」
可诸侯们并不是这么想的。
他们发现新都城离自己的领地更远,去朝见一次得走上十天半个月,东夷的首领们开始拖欠贡品,第一年还送来一半, 第二年就只送三分之一。
廑坐在空荡荡的仓库里,看着那些少得可怜的铜块和兽皮, 想起父亲当年摔碎的陶簋,他忽然就明白,迁都只不过换了个地方,根本没改变根本问题。
05 诸侯的影子
廑在位的第5年,淮夷完全不纳贡,使者带回来的消息特别简单, 「夷首说,夏后氏的德泽,到不了淮水。」
朝堂上,大臣们吵得跟一锅粥似的, 有的说该出兵去征讨,有的说该派使者去安抚,廑听着他们争论,眼睛瞅着殿外的青铜兵器架上,那些兵器还是父亲留下来的,很多年没使过,都蒙上灰尘了。
「王上。」老将跪着请求道,「给我三千兵,我准能拿下淮夷首领的脑袋。」
廑询问道, 「三千兵,粮草够不够,兵器足不足,要是淮夷联合风夷、畎夷一块造反,西河能不能守得住?」
老将被问得没话可说。
廑看向司农,问道,「今年粮食收成如何?」
司农跪着回禀,「比去年又少了一成。」
廑闭上了眼睛。
他想起二十五岁那年对妻子说的话, 「我不怕当王,就怕当了王之后,发现什么都没法改变。」这会儿,这话好像诅咒似的灵验了。
他做出决定, 「不出兵,派使者过去,带着最好的玉器和丝绸,问问淮夷想要什么。」
使者去了三个月,只带回来一句话,「他们要王亲自去淮水盟誓。」
孔甲在朝堂上大笑着说道,「王兄,这是侮辱,夏后氏的尊严在哪儿?」
廑平静地说道「尊严不能当饭吃,传令,准备船只。」
他生平第一回离开西河,沿着黄河往下走,随后又转去淮河,船行驶了七天七夜,他站在船头,看着两岸从黄土变为湿地,到了淮水边,淮夷首领带着好几千人排着队来迎接,不过没有跪拜。
廑下了船,光着脚踏上湿软的泥土,他对着首领说「我来了,你想要什么?」
首领是个满脸刺青的中年人「我们想要独立的祭祀权力,还想要夏后氏承认淮夷的长子继承制度。」
廑沉默了好一会儿,这两个要求,就好像在夏朝里头又弄个小朝廷一般,可他没有别的选择,
「行。」他说「但淮夷也得承认你们的祖先是夏后氏分支。」
这是他的底线。
首领思索了一下,点了点头表示同意,双方在淮水边杀白马立誓,廑亲手将一块刻着盟约的玉圭扔到水里头。
回西河的路上,妻子问他,「你恨吗?」
廑望着河面说「恨什么?」
「恨自己只能妥协。」
「不恨,」 廑说,「恨解决不了问题,父亲教我守成,不降叔父教我谨慎,可没人教过我,当一个王朝开始烂掉时,王该咋办」
他叹口气,「也许孔甲会不一样,他心气高,或许能……」
妻子打断他,「心气高会摔得挺惨的。」
「这是不降叔父的遗言」廑苦笑着说,「那我们姒家,总得有人去试试。」
06 病榻上的归途
廑在位的第7年,儿子病死了,那个身体弱多病的孩子,没熬过西河的冬天, 廑抱着他冰凉的小身子,在宗庙里坐了一整夜,他想起迁都那年,妻子抱着这孩子跟在自己后边的模样。
也许,他对妻子说「我不该带他到这里来,」
妻子已经哭不出眼泪了, 说道,「你是王,你想去哪里都行,可他就只是一个普通孩子。」
廑没什么话可说了,他忽然明白, 自己不光没守住夏朝的根基,就连自己的血脉都没保住了,
从那天起,他的身体就不好了,先是咳嗽,紧接着开始咳血,最后连站起来都困难了,太医说这是肺痨, 没有治疗的办法了,廑知道,这是心病。
廑在位的第8年秋天,天上出现了奇特的景象三个太阳并排挂在天上,中间那个明亮,两边的暗淡,史官赶紧跑过来记录,说这叫做幻日, 是上天在警告,
廑躺在病床上,透过窗户看着那天象,他想起了祖父泄,父亲扃, 叔父不降了,他们一辈子费力保持的夏朝,难道就要在他这里断掉吗
他下令说「传孔甲。」
当孔甲过来时,穿着非常华丽的丝衣,腰间的青铜剑已经换成带有黄金装饰的, 他站在榻前边,眼里忍不住有兴奋的神色说道,「王兄,有什么吩咐?」
廑让他靠近,然后指着案上的玉圭说, 「这是王的信物,我死了之后,你就继承王位吧。」
孔甲愣住了,说道,「您还有儿子…」
「没了」廑打断他,「都没了,不降叔父说得对,你的心气高,也许夏朝需要这样心气高的人,但是记着。」
他抓住孔甲的手腕,用最后那一点力气说, 「诸侯的心,要用血和德一起拴着,可别学我,就只会妥协。」
孔甲跪着接过玉圭,声音发抖地说,「好的……我,记住了。」
廑松开手, 看着窗外说,「西河的冬天可太寒冷,我死了之后,把我葬在向阳的山坡上,让我能看到洹水,看到田地。」
他停顿了好长时间,又开口说「让我能看到,你们会把夏朝带成什么样。」
那就是廑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
第二天凌晨,霜降按时到来, 把西河城给覆盖住了,廑王在睡梦中离去,手里还紧紧握着他父亲扃留下的那块玉圭。
他统治了8年,搬过一次都,调解过一次纷争,失去了一个儿子,留下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,史书上对他的评价就那么几句, 「守业不够,没什么革新的行动。」
可是,在西河城的工匠们中间, 有这么个传说,他们看见王亲自在大太阳下和泥筑城,看见王光着脚走在田埂上量土地,还看见王在失去儿子后,独自在城墙上走了一整夜。
这些细节没被写进正史,正史只记录王的功绩和过错,不记载王作为一个人的痛苦与挣扎,
07 历史注脚
廑王在位8年,迁都到西河,来应对东夷离心的情况, 最后传位给孔甲,这些基本事实能在《竹书纪年》以及《史记·夏本纪》的世系记载里看到。
夏朝中后期,王权衰落和部落离心是主要矛盾,廑王的妥协策略虽然保持了表面和平,却没能够阻止那个趋势, 这种守成不够的尴尬境地,体现了夏后氏统治的结构性危机。
对于他没有子嗣继位的记载,只是史料推断, 夏朝史料很少,没法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性,本文在重大事件的框架内补充日常生活细节,尽力展现一位处在王朝衰落时期的君主的真实生活。
创作说明:本文是基于历史的基本情况,开展的二次文学创作,部分属于虚构内容,仅供娱乐,注意甄别,图片为ai生成。
发布于:上海市倍盈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